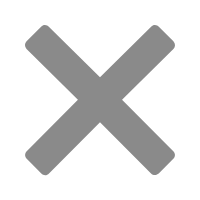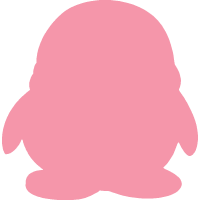-
后庭花
本书由讯读文学进行电子制作与发行 ©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第一章
新科状元郎那不染尘埃的样子,我很是看不惯,凭什么不染尘埃,干干净净一身白,又凭什么置身风波里,又在水火之外?
“你别坐高台,你要掉下来。”
后来啊我才知道。
他那么高不可攀的人,也会跪下来求我不要离开。
1
流苏阁是盛京有名的青楼,贵族商贾皆在此寻乐。
流苏锦帐双鸳鸯,梦魂醉入温柔乡。
我是这里的花魁,漾儿。
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此刻的我,正在台上悠然一舞,彩扇飘逸,飞燕游龙。
座上的人们看得如痴如醉,恨不得以千金买我斟一壶酒,以万金买我一夜春宵。
只是,“漾儿卖艺不卖身,还请各位公子另寻他处。”
我不在乎那些男人失望的神色,左右不过精虫上脑,酒囊饭袋。
我粗略看了一眼台上各家公子给的赏赐,捡了几件名贵稀奇的放进袖子里。
纵使青楼供吃供住,但不受男人们喜欢的姑娘生活依旧很艰辛,我得把这些东西典当了给姐妹们傍身。
最近几年被罚没到这里来的官妓,大多是被抄了家的贵门小姐,我也不例外。
我是前朝的公主。
我曾经叫姜封阳,其阳多赤金,其木多椒据,名字里尽是父帝母后的疼爱。
只不过如今,国不是国,家不是家,万人之上的公主,竟屈居青楼,哄男人开心。
“封阳!”
我听别人叫我漾儿听习惯了,突然有人叫我的闺名,反而让我不太习惯。
我猛地回头朝声音来源处看去。
那是一个男人,清颜白衫,长身玉立,与他周围的男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与这里格格不入。
我看不到自己此刻看他的眼神,不过纵然能看到,也不外乎仇恨与痛苦。
“呵,这不是刑部侍郎大人么?怎么今日有空来这儿寻开心?”
没错,来人正是刑部侍郎——傅知行。
“你别胡闹,我今日是与同僚一起来此议事!”
“议事?”
我笑了,谁家好人来青楼议事啊,“既然诸位大人来议事,流苏阁自然要款待周全,今天我做主,给大人们最好的包间,最美的姑娘!”
“封阳!”
“你住嘴。”
听傅知行再叫这个名字,我全身的刺都炸了起来。
他的同僚刚刚还看我温柔似水,突然变得暴戾起来,都愣了神。
“封阳,是我对不住你,可你也不必这般自轻自贱。”
“我说了,让你闭嘴。”
我压低声音,只有我和他能听到,“姜封阳已经死了,死在国破家亡的那天。”
我自轻自贱?
姜封阳这个名字该在前朝,该在后宫,就是不该在青楼里出现。
傅知行也愣在了原地,随即他调整好情绪。
“漾儿姑娘如此盛情,我们也不好推辞,多谢姑娘。”
我看着他脸色苍白又强装镇定的样子,恢复了之前的巧笑倩兮,“那大人们跟我来!”
我带他们去了流苏阁的天字包房,嘱咐小厮上最好的菜,上最名贵的女儿红,并且叫了阁里最美最美的姑娘们来伺候。
姑娘们很识大体,自觉围着一堆高官们斟起了酒,哄得他们欢笑阵阵,却没人坐在傅知行身边。
因为傅知行不仅是当朝刑部侍郎,还是前朝的新科状元郎——我那未成婚的驸马。
傅知行端坐在同僚和姑娘们中间,抬首看我。
我也这么静静看着他,他的眼里有歉意,有愧疚。
只是,一切都晚了。
我与傅知行,怕是一段孽缘。
彼时,我还是娇宠的封阳长公主,虽养在深宫,但自是谋略女工样样精通的,更不提容色出众,仪态雍容。
天下皆凡人,封阳长公主无一人能配的名号,早已传开。
我及笄之时,多少名门子弟望而却步,不敢入宫提亲。
那年元宵夜,恰巧我女扮男装便衣出宫游玩,在盛京最繁华的天街上,撞到了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。
他眉如墨画,冠如宋玉,靛蓝色的衣服不新,却衬得他脸色更干净白皙。
他与我见过的所有男子都不同,他身上没有那些贵气,却有着青松一般的正气。
他正是傅知行。
傅知行的书被我撞落一地,我赶紧低头去捡,慌乱中,我束发的簪子被他撞掉,一头乌发倾泻而下。
盛京天街,人声鼎沸。
那晚的月很明亮,那晚的灯也很耀眼。
可我只记得他面上带着比刚刚更慌张的神色,微微拱手,用温润的声音说道,“小生举止无状,叨扰姑娘了。”
我失神了一瞬,很快便想起头发还散着,忙寻掉落的簪子。
人海茫茫,哪里还寻得到?
傅知行这时拔下了他头上固定冠的竹簪,递给我,“姑娘若不嫌弃,先用这个吧!”
我接过,行了一个女子的礼道谢,“公子家住何方姓甚名谁?我好将簪子还您。”
“小生进京赶考,并无住宿,簪子姑娘不用还了,就当我送姑娘的赔礼吧!”
“赔礼?”
当时的我根本没反应过来,明明是我先撞掉了他的书。
后来回宫后,我细细观察那枚竹簪,不像是市面上卖的,反而像是自己削的。
竹簪刚直端方,和他一般。
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,也不知道他的住址,只知道他是新入京的举子,那年的我,对科举一事格外重视了些。
一日,我陪父帝母后一同用膳,正听到他们谈起科举的事情。
父帝说,今年有一个举子特别出色,诗书礼义无所不达,长得也好,像块玉石。
我鬼使神差地问,“这举子叫什么?”
“傅知行。”
我不知道那夜遇到的男人叫什么,可我却莫名觉得这个名字很配他,“父帝可属意他为状元?”
“正有此意。”
“那封阳也想去看看新科状元郎长什么样子!”
“哈哈好啊,若是那些俗子封阳看不上,自然可以在这些举子里择一个好的当驸马!”
父帝向来宠我,对我无所不依。
我却害羞地不再接话,因为我确实对那夜遇到的那个举子动了心。
榜单张贴出来时,状元榜眼探花是要穿红游街的。
探花、榜眼、状元骑马鱼贯而出,道路两边围满了老百姓,想看看未来国之重臣的样子。
那天我站在紫禁城城墙上,既想看又不想看。
想看是因为想看他,不想看是因为怕看到的不是他。
我朝城下看去,状元郎骑在枣红马上背部挺直,正让人想到“君子端方”这个词。
再仔细一看,正是那夜我撞到的那个男人,大红色的状元袍,比靛蓝色的外袍更衬他。
我和父帝说明了自己的心意,父帝自然是欣喜的,他也认为傅知行确实是一个可塑之才,品行也配成为一国长公主的驸马。
只是不知道傅知行是不是有意中人或原配妻,还要父帝去问。
父帝召他进宫,说明了要为他赐婚的消息,傅知行竟然推辞了。
他说,男儿应当先立业,再成家。
如此推拒,父帝也不好勉强,只得说那便为新科进士在御花园设宴,让傅知行必要参加。
我知道,这是要让我们见上一面,看看是否能扭转傅知行的心意。
状元宴那日,天气正好,晴空万里,我盛装打扮,心中却忐忑。
宴饮过半,我想去御花园里醒醒酒,行至一半,正巧看到傅知行。
他一身红袍立于梨花树下,红白相映,分外清秀。
我鬼使神差地走上前去,“傅大人,别来无恙否?”
听到有人说话,还是女眷,傅知行立刻认识到御花园中皆是帝王家眷,他顿时低下头去拱手作揖,拜到一半,突然意识到我问的是“别来无恙否。”
他慢慢抬头,我正笑意嫣然看着他。
“是你?”
傅知行好像很惊讶,“你是......”
我猜他可能将我当成某位妃子了,可他转念一想,若是妃子,必然不可能随意出宫。
“本宫是公主。”
说着,我将放在他身上的视线收回挪到了梨花树上,然后折下了一枝梨花,“就是被你拒婚的那个公主。”
傅知行恍然大悟,随即从脸开始红到了耳朵根,“臣不知是公主。”
“你是不知道本宫是公主,还是不知道公主是本宫?”
我这话说得露骨,傅知行自然知道。
我本没打算等他回应,可他沉默了两秒,竟道,“臣不知公主是您。”
这话便是同意了婚事,也认定了我。
我将折下的那枝梨花,就手别在了他的头上,“我叫姜封阳。”
傅知行本就是新晋状元郎,如今又是封阳长公主未来的驸马,一时间身价大涨,炙手可热。
再后来,便是国破家亡了。
我还记得那一日,本平平无奇,只是父帝母后突然让我离宫避难,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,坚决不走。
后来我才知道,谋反由来已久,父帝怕我担心,始终没有与我说。
叛军来势汹汹,却没有伤平民百姓一根毫毛,父帝仁孝治国,我不知他们为何谋反。
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,叛军其实是前朝余孽。
从他们的视角来看,他们夺回的是自己的江山。
在叛军还未攻进紫禁城前,父帝召见傅知行,要他带我离开,远走天涯,说这是他给傅知行下的最后一道圣旨。
傅知行自是遵从的,只是他来永安宫接我一同离开时,我挣扎了一些,向来温润如玉的他,直接将我敲晕了。
再后来等我醒来,我并未出宫,而是与父帝母后一同被关进了大牢里。
我身边不见傅知行,不知他去了哪里。
在牢中浑浑噩噩过了几日,新帝登基,百废待兴。
新帝于百忙中下了对我们的旨意,我被充做官妓,父帝母后择日处斩。
我悲痛欲绝,想请求他们绕过父帝母后性命,父帝却让我永远不要对敌人求饶。
再后来,父帝和母后问斩那天,新帝变态一般让我去送他们最后一程。
刑场上,我竟看到傅知行坐在上首,他投靠了新帝,作为新科状元郎,被新帝封为刑部侍郎,委以重任。
我的驸马成了叛国贼、亡国奴。
神思转回,傅知行还坐在那里定定看着我,我转身便走。
“封......漾儿,你......去哪儿?”
“自然是看看有没有哪位公子找我。”
我说这话时,他分明皱了皱眉。
“怎么?傅大人是想让小女子作陪?”